回忆过往,我的生活似乎是一个镶满珠宝的美好传说,一片铺满鲜花的芳草地,一个每时每刻都充满爱和幸福的阳光灿烂的早晨,这样的日子难以用言语表达其中的欢欣和喜悦,我创办学校的理想是我的伟大成功,我的艺术熠熠生辉;然而,还有一些日子,当我回忆起来时又觉得厌恶而空虚,那时的过去仿佛是一场灾难,连未来也充斥着不幸,而我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疯子的妄想。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谁能了解?恐怕上帝自己也迷惑不解吧。在这痛苦和欢乐之间,在这幽暗的污秽和光亮的纯洁之间,在这既装载着地狱之火又闪耀着英雄主义和美的血肉之躯中,生命的真谛究竟体现在哪里?不管上帝还是魔鬼都未必知晓。
因此,在类似的冥想中,我的思绪就像穿过一扇镶着彩色玻璃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有时看到的是美好而丰富多彩的景观,有时看到的只是平淡而黯淡的景象。
如果我们能够像潜水员那样深入自己的内心,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深入我们的灵魂采撷深处的珍珠,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我努力奋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我只希望重返巴黎,在那里我或许可以变卖财产而获得一些钱。当时,玛丽正从欧洲回到美国,在比尔特摩给我打来电话。我将目前的窘境告诉了她,她说:“我的好友戈登·赛尔弗里奇明天就要起程了,我跟他说说,他肯定能帮你弄到一张船票。”
 戈登·赛尔弗里奇,美国实业家、零售业巨头,并在伦敦成立了赛尔弗里奇百货公司
戈登·赛尔弗里奇,美国实业家、零售业巨头,并在伦敦成立了赛尔弗里奇百货公司这次的美国之行令我心力交瘁,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玛丽的提议。第二天上午,我从纽约搭船,离开美国。当天晚上,我遇到不幸。由于战时条件有限,船上没有点灯,我在漆黑的甲板上行走时,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约15英尺的缺口中,身受重伤。戈登·赛尔弗里奇不但慷慨地把自己的舱房让给了我,还时常陪伴我,他真是一个友善而优雅的人。我告诉他自己第一次见他时的情形。那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小丫头,找他赊账卖给我一件跳舞时穿的衣服。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实业家。在接触了那么多艺术家和梦想家之后,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令我大开眼界——他是一个纯然阳刚的人,而我的恋人们却带有明显的阴柔气质。另外,我身边的男人们多少都有些神经质,不是深陷忧郁,就是醉酒狂欢,赛尔弗里奇却是我见过的人之中最非凡、最快活的人。他滴酒不沾,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还会有人在生活本身中体验到快乐。我以为,未来的生活只有通过艺术和爱才能时不时地透露出瞬间的欢乐,这个男人却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快乐。
抵达伦敦后,我的伤仍未好,也没有钱去巴黎,只好在公爵大街租了一个住处,并给巴黎的几位朋友发了电报。可能是战争的缘故,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在那间沉闷的房间里度过了惨淡的几个星期,完全走投无路。我一个人,带着伤,没有钱,我的学校散了,战争似乎没完没了。夜里,我常常坐在漆黑的窗边看空袭,真希望有一颗炸弹落在我身上,结束我所有的苦难。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不止一次地想要自杀,但是有一股力量牵着我往回走。如果药店出售自杀药像出售预防药一样寻常的话,我想世界上的知识分子为了克服痛苦,肯定会去买自杀药,然后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
我在绝望中发了电报给洛亨格林,却杳无音信。我的学生想在美国寻求发展,一位经理人为我的学生安排了一些演出机会。她们后来便以“伊莎朵拉·邓肯舞团”的名义到处表演,但是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幸好在一位法国大使馆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才回到了巴黎。我在巴黎的奥赛宫租了一个房间,从放债人那里借了一些钱勉强度日。
每天清晨5点,我们都会被巨炮发出的残酷的轰隆声惊醒,以此开始不幸的一天。从早到晚,前线不断传来可怕的消息,死亡、流血、屠杀充斥着每时每刻,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在夜晚分外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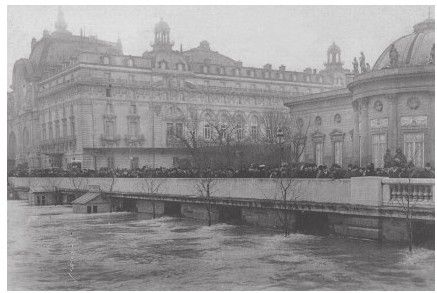 巴黎奥塞宫
巴黎奥塞宫这段日子虽然暗淡无光,却也有一个美好的记忆。一天晚上,我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巧遇了著名“王牌”盖洛斯。当时他在弹奏肖邦的音乐,而我在跳舞。离开朋友家后,他便陪我从帕西走向奥赛宫。在路上,我们刚好碰上了空袭,却像没事人似的驻足观看。轰炸声不断,我在协和广场为他翩翩起舞——他则坐在喷泉边为我喝彩,沉闷的黑眸里闪烁着火光,要知道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那晚,他对我说,他但求一死,别无他求。此后不久,“英雄的天使”找到了他,将他带走了——与这个他所厌恶的世界彻底告别了。
日子单调地重复着。我倒是很想当护士,可是申请当护士的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似乎少我一个也不会怎么样。我决定还是重返艺术的怀抱吧,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双脚能否承载沉重的心灵。
我很喜欢瓦格纳的一首曲子——《天使》,说的是一个人在哀伤寂寞中孤坐着,最后光明天使来到了他的身边。在这些灰暗的日子里,当一位朋友带着钢琴家瓦尔特·隆梅尔来见我时,就像歌曲中的光明天使来到了我的身边一样。
他进来时,我以为是年轻的李斯特从画框中走了出来——身材高大,形体瘦削,饱满的额头上垂下一缕光亮的头发,双眼炯炯有神,宛如两口清澈的水井。他为我演奏。我唤他为我的大天使。雷雅纳慷慨地腾出剧院的休息室,我们便在那里工作。当巨炮在狂轰滥炸时,当战争消息不断散播时,他为我演奏李斯特的《在荒野中冥想上帝》。这首曲子里,圣弗朗西斯与鸟儿们和谐对话。我受到启发,创作出新的舞蹈,表现了祈祷、甜美和光明。他的手指碰触着琴键,弹奏出天籁般的旋律,令我的精神再度飞升,重获生命力。我人生当中最神圣、最美妙的一段爱情由此拉开序幕。
还没有人能够像我的瓦尔特·隆梅尔那样演奏李斯特的音乐。他的洞察力和感受力非同一般,能够超越乐谱,看到音乐的真正狂热——那种每天与天使对话的狂热。
他温柔、甜美,同时又燃烧着激情。他以惊人的狂热弹奏。他的神经吞噬着他,他的灵魂在反叛。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不由自主地屈从于激情的旋涡。相反,他对激情既无法抗拒又厌恶至极,两者都一样显见。他俨然是一个在燃烧着煤炭的火盆上跳舞的圣者。爱上这样一个男人是危险的,同时也是困难的,因为对爱情的厌恶之情很容易转变为对爱人的仇恨之情。
经由血肉之躯来接近一个人并发现他的灵魂,经由血肉之躯找到欢愉、激情和幻想,这一切是多么怪异又可怕啊!哦,寻找人们称为幸福的感觉——经由血肉之躯,经由外在容颜,经由人们所谓的爱情——尤其如此。
你们别忘了,我的这些记忆跨越了很多年。每一位新的爱人向我走来时,不管他是魔鬼、天使还是平常人,我都相信他就是我长久等待的那个人,相信这份爱将会成为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升华。我想,爱情来的时候,总是让人如此坚信吧。我生命中的每段恋情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只不过小说的结局往往很悲惨。我一直在等待有一段结局圆满的恋情,一段长长久久的恋情——就像那些大团圆电影里演的那样。
爱的奇迹就在于其丰富的主旋律和多变的基调,能以不同的方式弹奏。一个男人的爱与另一个男人的爱是无法比较的,就像贝多芬的音乐与普契尼的音乐是不同的;女人则是回应这些爱之演奏者的乐器。我认为,一个女人只爱一个男人,其情形类似于终生只听一个作曲家的音乐。
夏天越来越热了,我们前往南方的一个安静的避暑胜地,住在费拉角圣让港附近的一家乏人问津的旅馆里。我们将闲置的车库改为工作室,从早到晚,他演奏着天籁之音,我翩翩起舞。
 陪伴伊莎朵拉的钢琴家瓦尔特·隆梅尔
陪伴伊莎朵拉的钢琴家瓦尔特·隆梅尔多么美妙的时光啊!瓦尔特·隆梅尔陪伴左右,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整天徜徉在音乐的怀抱里,我的生活就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死后升入天堂般幻然若梦。生活是一个钟摆——痛苦越深,狂喜越强。每一次沉落在悲伤的深渊之后,便会被抛向更狂烈的欢乐。
我们时不时地走出避暑胜地,为那些不幸者举办义演,或者为伤者举办音乐会。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喜欢独处,从音乐的交流到爱情的交融,再从爱情的交融到音乐的交流——我的灵魂栖息在幸福的制高点。
附近的一幢别墅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和他的妹妹吉拉尔德女士。牧师曾经在南非当过传教士。他们是我们仅有的朋友,我常常在李斯特的神圣乐曲的启发下,为他们跳舞。夏末的时候,我们在尼斯找到了一间工作室。宣布停战后,我们又回到了巴黎。
战争结束了。看着生力军的队伍穿过凯旋门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高喊:“世界得救了。”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全都变成了诗人。但是,唉,即使是诗人也要清醒过来,为所爱的人张罗面包和奶酪,我们的世界必须醒来,恢复生产。
 一战结束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穿过凯旋门
一战结束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穿过凯旋门瓦尔特·隆梅尔牵着我的手,一起去贝勒维。我们发现房子已经倒塌,成为废墟。那么,为何不重建呢?于是,我们花了数月时间筹集资金,妄图重建学校。然而,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了。
最后,我们终于相信,这件事断难实现。法国政府开出合理的价格,收购了我的学校。他们计划将这幢大房子改建成生产使人窒息的各类毒气的工厂,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当初我的“狄俄尼索斯殿堂”成了救助伤员的医院,而今我又注定要放弃它,让它沦落为生产杀人器具的工厂。失去贝勒维是一大遗憾——贝勒维啊,那里的风景多么美丽!
买卖手续终于办妥,款项也存入了我的银行账户。我在庞培路买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原先是贝多芬音乐厅,我将它变为工作室。
我的瓦尔特·隆梅尔有一颗怜悯之心。那些让我身心疲惫、夜不能寐、以泪洗面的痛苦,他似乎都能感同身受。每当这些时刻,他总是用无限怜爱和充满光亮的双眸注视着我,给我莫大的安慰。
在工作室里,我们俩的艺术神奇地合二为一。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舞蹈变得更加轻灵。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弗朗兹·李斯特音乐的全部内涵。我们根据李斯特的音乐创作了一出独舞。在贝多芬音乐厅静谧的音乐室里,我开始研究一些著名壁画上的人物动作和光线处理,希望用到《帕西法尔》的表演中。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配着我们,将我们的灵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跳舞他弹琴的时候,或者我伴随着他弹奏的《圣杯》的悠扬的银色旋律举起双臂、灵魂缓缓飞出身体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似乎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存在。当音乐和舞姿不断向上延展,飘至浩瀚无垠的境界时,天穹似乎传来了回音。
我相信在这些音乐时刻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让我们两个人的灵魂在爱情的神圣能量中琴瑟合鸣,仿佛到达了另一个世界的边缘。观众们也感受到了这股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且一种奇异的精神张力常常弥漫在剧院里,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如果我和瓦尔特·隆梅尔能够进一步探索下去,我确信这种精神力量会引导我们实现自然舒展的境界,为人类带来全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对最高形式的美的神圣追寻,竟因世俗的激情而夭折,多么可惜啊!正如传奇故事所言,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为邪恶的妖精敞开大门,结果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也是如此。我没有满足于追求眼前的幸福,而是重新燃起了创办学校的念头,为此发了电报给远在美国的学生们。
她们来到我身边后,我召集了一些忠实的朋友,提议说:“我们一起去雅典吧,去看看雅典卫城,或许还能在希腊建一所学校。”
没想到我的初衷完全被误解了!《纽约人》(1927年)上有位作者如此评价这次出行:“她真是挥霍无度。她在别墅里搞了几天几夜的宴会,然后从威尼斯出发,直奔雅典。”
可是,我多么不幸!我的学生们来了,她们年轻漂亮,事业有成。我的瓦尔特·隆梅尔看着她们,爱上了其中的一个。
 雅典的札皮欧宫
雅典的札皮欧宫我该如何描述这一次葬送了爱情的旅行呢?我们在利多的埃克塞尔斯瓦酒店住了几个星期,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他们的恋情;随后乘船前往希腊,我确信了他们之间有恋情。这件事让我深受打击,即使月光下的卫城再美丽,也无法打动我的心——这就是我的爱情一步步走向终结的过程。
到达雅典后,我的建校计划似乎进展很顺利。韦内洛斯慷慨地让我们使用札皮欧宫。这里成了我们的工作室。每天上午,我与学生们在此工作,努力启发她们跳出与雅典卫城相匹配的舞蹈。我计划为即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办的酒神节庆典活动训练出一千名舞者。
 美国摄影家、画家爱德华·斯泰肯
美国摄影家、画家爱德华·斯泰肯我们每天都去雅典卫城。我依然记得1904年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而今看着年轻的学生们的舞姿,我觉得16年前的梦想至少实现了一部分。我情不自禁地百感交集。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应该能够在雅典创办起一所梦寐以求的学校了。
我的学生们在美国待了太长时间,沾染了某些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习气,令我很不快。然而,在雅典辉煌的天空下,她们受到山峦、大海和伟大艺术的感召,逐渐将身上的不良习气涤荡干净。
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与我们同行。他在雅典卫城和狄俄尼索斯剧院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我梦想在希腊实现的盛景状况,在这些照片中隐约可见。
科帕诺斯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牧人和他们的山羊群留在那里。不过,我并没有气馁,很快就鼓足干劲,决定清扫场地、重建房子。我们的重建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囤积多年的垃圾被清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帮我们安装了门窗、搭建了屋顶。我们在宽敞的客厅里铺上了适于跳舞的地毯,接着又安放了一架钢琴。每天下午,当夕阳沉落在卫城的背后,将柔和的紫色、金色光芒投射到大海上时,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便弹奏起优美动人的音乐——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作品。到了凉爽的夜晚,我们头戴从街上卖花的雅典男孩那里买的可爱的白色茉莉花环,悠闲地走下山,到法勒隆海边吃晚饭。
置身于这群头戴花环的姑娘们中间,我的瓦尔特·隆梅尔就像帕西法尔站在昆德丽的花园里。我留意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新表情,更像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因为有了智慧和精神的强大融合而坚不可摧;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那对闪亮的羽翼已经变成了一双热情的手臂,用以抓牢和抱住德律阿得斯的身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以前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无法帮助我摆脱磨难。
从那个时候开始,惶恐不安的痛苦将我包围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窥探他们日益加深的爱情。令我恐惧的是,我如此嫉妒,竟然萌生了类似于谋杀的邪念。
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他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平常人了——刚刚弹奏完《众神的黄昏》中那段恢弘的进行曲,余音还在空气里缭绕,似乎要融入落日紫色的余晖中,呼应着海默突斯山,照亮了整片大海。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们四目相对,彼此眼中燃烧的激情堪比灿烂的落日。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勃然大怒。如此激烈的反应,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转身就走,整晚都在海默突斯山附近的小山上游荡,无法排解内心狂乱的绝望。我以前就知道,绿眼魔怪的毒牙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可是到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痛苦居然强烈至此。我无法自拔,生不如死。我爱他们,同时,我也恨他们。这种体验,让我理解了那些被嫉妒蒙蔽了心智而杀死情人的可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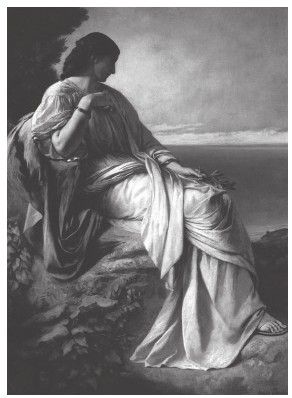 伊芙琴尼亚,迈锡尼王阿迦门家的女儿
伊芙琴尼亚,迈锡尼王阿迦门家的女儿为了不让自己落入如此田地,我带着一小群学生和朋友爱德华·斯泰肯踏上了一条神奇的道路,经由底比斯古城,到达卡尔基斯。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片金色的沙滩,想象着在伊芙琴尼亚不幸的婚礼上,一群埃维厄岛少女正是在这里为她跳舞庆祝。
那个时候,希腊所有的荣光都无法驱走我内心盘桓着的魔怪。这个魔怪不停地将留在雅典的那两个人相处的画面展现在我的面前,噬咬着我的要害,像硫酸一样腐蚀着我的大脑。回到雅典后,当我看到他们靠在卧室外的阳台上如胶似漆的模样时,他们的青春和爱火再一次将我推向痛苦的深渊。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无法理解自己当初的执狂了。但是在那时候,我已经深陷其中,就如同患上了猩红热或者天花这样的纠缠不清的疾病。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给学生们授课,继续进行在雅典建校的计划。建校的进展情况很顺利。韦内塞洛斯政府十分支持我的计划,雅典人民也热情高涨。
一天,我们应邀前往大型露天体育场,参加为韦内塞洛斯和年轻的国王举办的庆典活动。5万人拥向体育场,希腊所有的教会也都来了。当年轻的国王和韦内塞洛斯进入体育场时,全场爆发出热情的欢呼声。主教们的队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身穿金丝绣线的挺括的锦缎长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穿着有褶皱的柔软的束腰短裙走进体育场,身后跟着一群学生,她们是活生生的塔纳格拉雕像。康斯坦丁·梅拉斯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为我戴上桂冠,说:“你,伊莎朵拉,将菲迪亚斯不朽的美和希腊辉煌的时代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回答说:“啊,请帮助我培养出一千名优秀的舞者。届时,她们将在这个体育场翩翩起舞,场面极为壮观。全世界的人都会过来欣赏她们的表演,发出惊喜的赞叹声。”
我说完这番话时,看到他兴奋地握着他情人的手,刹那间,我感到自己释然了。与我伟大的理想相比,这些个人情绪算得了什么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爱惜和宽容。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我看见他们相互依偎在阳台上,两颗脑袋靠得很近,在月光下卿卿我我,我便又成了渺小的个人情绪的俘虏。我心乱如麻,独自在外面游荡,差点就像萨福那样从帕台农神庙前的巨岩上跳下去。
这种痛苦的情绪折磨着我,令我苦不堪言。景色怡人,只徒增了我的不幸。我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难道我们伟大而神圣的音乐合作计划就这样在世俗的情感纠缠面前破灭了吗?我不可能要求这名学生离开,毕竟她从小就在我的学校里长大。可是要我每天看着他们深情款款的样子,还得克制内心的苦恼,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进退两难。当然,我也可以试着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眼前这一切。我虽然不快乐,但是依旧进行着舞蹈训练,去山野远足,每天到海里游泳。我凭借这些活动保持了胃口,却仍然难以遏制世俗情感的激流。
我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我努力教学,将美、沉静、哲学以及和谐的思想传递给她们;另一方面,我的内心却承受着莫大的煎熬。这种状况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我无从知晓。
我只能强颜欢笑,故作坚强。每天晚上在海边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喝大量的希腊烈酒,以此麻痹自己的痛苦。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来疏解我的痛苦,只可惜我当时已然昏了头。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我个人的悲惨经历,我现在只是设法记录下来。有价值也好,无价值也罢,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反面教材”,让大家引以为鉴。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远离灾祸、排解痛苦。
在命运的安排下,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最终以一个奇怪的事件宣告结束。起因是一只可恶的小猴子咬了人。它咬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国王,这令他危在旦夕。
年轻的国王在死亡线上徘徊了好几天,之后便传出了他驾崩的悲惨消息。国王的去世造成了国内局势动荡,甚至还引发了革命,韦内塞洛斯和他的政党被迫下台。这次事件也导致我们在希腊待不下去了,因为当初我们是作为韦内塞洛斯的贵宾受邀来到希腊的,现在则不得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有用于重建科帕诺斯和布置工作室的钱都白花了,我们只能放弃在雅典创办学校的理想,坐船离开希腊,经由罗马返回巴黎。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1920年的最后一次雅典之行,回到巴黎后的痛苦,跟瓦尔特·隆梅尔的正式分手,以及跟瓦尔特·隆梅尔和那位学生的最终分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异常痛苦的回忆。虽然我认为自己是这次经历的受害者,可是她的想法却截然相反。她刻薄地指责我的感情,还责怪我为什么不尽早放弃这段感情。
最后,我一个人置身于庞培路的那幢房子里。看到贝多芬音乐厅已经改装完毕,只等瓦尔特·隆梅尔在那儿演奏,我的绝望难以言表。这幢房子过去曾带给我无尽的欢乐,如今却令我无法面对。我的内心滋生出远飞的欲念,想要飞离这幢房子,飞离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世界和爱情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人的一生会有多少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啊!然而,要是我们能够将视线拉长,望向山的后头,便会看到那里有开满鲜花的山谷等待着我们去欣赏,以及美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追求。我很排斥很多女人的论断,她们认为女人年过四十后,就应该摒弃所有的爱情生活,维持表面的庄严和体面。哈,多么荒谬的想法!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进行着奇异的旅程。在此期间,感受自身躯体的变化真是妙不可言!首先是害羞、胆怯、纤瘦的年轻姑娘的身体——我也曾年轻过,慢慢成长为强壮坚毅的亚马逊女战士。随后,我们变成了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沉浸于酒的芬芳里,无法抗拒萨梯的爱抚,身体变得温润,生长着、膨胀着;柔软、性感的肉体愈加丰盈,乳房敏感到能够回应极为漫不经心的爱意,并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快感传遍整个神经系统;爱,如今成长为一朵盛开的玫瑰,充满质感的花瓣紧紧地包裹住落入其中的猎物。我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宛如一个精灵生活在云端——那燃烧着玫瑰般火焰、呼应着同类火焰的云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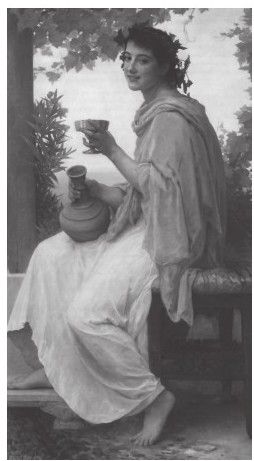 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
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只歌颂爱情和春天是多么无聊啊!秋天的颜色更加灿烂、更加丰富,秋天的欢乐更加强烈、更加骇人、更加美好。我同情那些囿于苍白、狭隘的信条的可怜女人,她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秋天之爱的慷慨馈赠。我可怜的母亲即是如此。因为这荒谬的偏见,她任由身体在本该尽情绽放的时期里衰老、生病,曾经智慧过人的大脑也逐渐迷糊了起来。以前,我是胆怯的猎物;随后,我变成了勇敢的酒神女祭司;而现在,我像大海拥抱畅游者那样拥抱住我的爱人,以云朵和火焰般的情怀一浪连着一浪地将他包围,让他旋转,与他水乳交融。
1921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维埃政府的电报:
只有俄国政府能够理解你。来吧,我们愿意为您创办学校。
这封电报来自何处?地狱吗?不是地狱——不过离地狱也不远。对于欧洲人而言,哪个地方最像是地狱?当然是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我环顾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没有了瓦尔特·隆梅尔,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爱情。于是,我回电说:
好的,我将前往俄国,我将教授你们的孩子。但有一个条件,即你们必须为我准备一个工作室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支持。
他们同意了。
我登上了一艘航行在泰晤士河的轮船,离开伦敦,取道塔林,最后抵达莫斯科。
在伦敦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算命师。她对我说:“你将远行。
 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
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你将会有许多奇妙的体验,你将遇到烦心事,你将结婚——”
听到“结婚”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笑着打断了她。我向来反对婚姻,又怎么会结婚?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算命师说:“等着瞧吧。”
在前往俄国的旅途中,我觉得自己就像复生的灵魂,向另一个星球飞升,欧洲的所有生活已被我抛诸脑后。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柏拉图、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梦想过的理想国家诞生了。我在欧洲为了实现艺术理想而倾注的精力全都化为乌有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征程。
我没带任何服装。我甚至能想象自己身着红色法兰绒上衣,与同样穿着朴素、情同手足的同志们共度余生的情形。
 邓肯与俄国诗人谢尔盖·叶塞宁
邓肯与俄国诗人谢尔盖·叶塞宁轮船向北驶去。我回头望向渐渐远去的资本主义欧洲,对其所有的旧制度和旧习惯报以轻蔑、同情的目光。从此以后,我将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为这一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实现宏伟的目标。那么,别了,这个不平等、不公正、野蛮冷酷的旧世界;别了,这个容纳不下我的学校的旧世界。
当轮船抵达目的地时,面对这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我万分激动。这个同志们相亲相爱的新世界,这个佛陀构想过的理想世界,这个耶稣基督描述过的理想世界,这个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向往的理想世界,这个列宁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理想世界,如今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工作和生活将成为这个理想世界辉煌远景的一部分。
别了,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到来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