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佘女士所做第一次口述记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第1期上,受到我几个朋友的批评,除了对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外,一位朋友尖锐地批评我在访谈前“案头工作没有做足”,这篇访谈完全是被被访者牵着走,也因此而归于失败。于是,我只好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在预先准备好一些问题之后,于2003年7月19日,又对佘女士做了第二次访谈。再做时虽然恰逢佘女士痛失爱子,情绪非常激动,但对我还是相当配合,对我的回答虽然简短,但基本上也还坦率。我也明确告知他们,我并不是记者,来为他们做访谈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任何人做宣传,而仅仅是学术研究而已,他们对此亦表示理解。
我两次拜访佘女士,时间相隔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我曾于2002年8月再次造访过东花市斜街的佘女士旧居,但见这一带的民居已荡然无存,唯存一片工地,在这里施工的工人告知,“佘老太太”每隔三两天就会来看一看,“你们真要找她,就在这里耐心盯上几天,准会见到”。而我当然不可能蹲守那里,所以又越明年,我才得以造访她的新居。从我的第一次拜访到本书定稿,转眼竟已过了6年。这么多年,这个故事曲曲折折,而且看来还会延续。然而,无论故事会怎样延续,从相关的文字记载入手进行考察,也还是必要的,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目前的众说纷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解释。
1.清代至民国文人对佘义士史事的记载
有关佘义士守墓之事,有文字留存于世的,我见到的有三种,兹引录如下:
第一则,清人笔记所记京师坊间相传的佘家守墓一事:
明袁督师(崇焕)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人敢收其尸者,其仆潮州人余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余某子孙,代十余人,卒无回岭南者。当时督师被执,廷臣力争,怀宗不悟。我朝深知其冤,乾隆间赐谥荫嗣,彰阐忠魂,千古未有。岭南冯渔山题义庄有云:“丹心未必当时变,碧血应藏此地坚。”
这则记载出自《燕京杂记》,该书未著撰者姓名,也没有撰著时间,但从文中称清朝为“我朝”来看,为清亡之前作品无疑,198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点校出版,前言称作者可能是清嘉庆以后的河北顺德人(见117—118页)。
第二则即张伯桢撰《佘义士墓志铭》:
大明袁督师之仆曰佘义士,粤顺德马江人也。执役于督师。督师出必挈之行。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朝廷非罪杀督师,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师墓葬。
第三则,张伯桢之子张次溪著《燕京访古录》,其卷五记:
(袁崇焕)暴尸于市,其仆潮州佘氏窃负其尸,藁葬广渠门内,即今广东旧义园中,守墓终身;比卒,乡人义之,遂附葬其右。至今守墓者皆佘氏子孙。
三者相较,大处相同,如佘义士行迹、袁崇焕尸被葬地点以及守墓者皆佘氏子孙等。不同的,除记述互有详略以外,比较明显的是一处细节,即佘义士的籍贯。清人文与张次溪文都说是潮州人,唯张伯桢称是广东顺德人,而佘女士说自己的老家是顺德马岗村人,认为说潮州是错的。我由此推测:张伯桢所记佘家之事,很可能并非来自佘家,而本于清人笔记。但张与他的友人们既然与佘女士的伯父或直接或间接地有过交往,会知道佘家的籍贯为广东顺德,遂按佘家人说法,很可能会据此对佘义士的出生地予以改订。但张伯桢之子张次溪的记述,语气与清人笔记一致,至于他为何采用清人说法而不取其父的修订,殊不可解。前面还谈到,此墓志铭是1917年张伯桢修袁督师庙时,刻于庙内中屋南墙上,而并非位于佘家为之看守的袁崇焕坟墓之旁,也说明此事经由文人彰显的可能性显然大于民间的口耳相传。
佘女士口传的故事,与这三段文字记载相比,歧异之处主要有二。
第一是三段文字记载讲的佘义士所盗,都是袁大将军之尸,而佘女士说的是头。关于袁崇焕头颅的下落,《明史》没有交代,唯张岱《石匮书后集》记:“……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卷十一),但也不知所由。所谓盗头,看来并无根据,很可能是口传的走样。此外如佘义士究竟是袁崇焕的仆人还是谋士,说法各异,佘家人当然愿意说得更体面些,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处就比较重要了,即张氏父子均未提到、唯清人笔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迄今守庄者皆余某子孙,代十余人”。到清朝中后期尚且是“代十余人”,虽算不上泱泱大族,却也不能说是人丁稀薄,这便与佘女士所谓其家代代单传的说法相左了。有关人士对佘家故事将信将疑的原因,就正出自这里,他们认为佘女士所谓的十七代,一则没有族谱等文字资料作为证据,二则从时间上算也不太相符,三是几百年的漫长年月,其间会有多少枝枝蔓蔓,哪里会如此直线一样的简单。所以佘女士所述世系,顶多从她本人上溯三代还有可能是真实的。这种怀疑确有道理,从佘义士盗袁尸的1630年算起到1939年出生的佘女士,300多年经历17代,未免迅速了一些,我在第二次访谈时追问佘女士第十四代佘淇之上的世系,原因也在于此,我甚至怀疑是有人将“代十余人”理解为十余代,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定:咱们排一排您家这十七代。
佘:我十四代的先祖叫佘淇。十五代是我爷爷佘恩兆,十六代是我伯父佘汉卿,父亲佘选增。十七代就是我了。我还一个堂哥,叫佘宝林,两个堂姐一个叫佘幼玲,一个叫佘幼兰。他们现在还在。
定:十四代再往上您还能数么?
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就失传了。
第三是我所见《燕京杂记》中的“潮州人余某”均作“余”而不是“佘”,我用的是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点校本。从所记事实与后来守墓者均姓“佘”来看,应是该本的笔误,至于是原文笔误还是点校本之误,尚有待查考。
此事有可能出自文人彰显,还有一事可证,那就是佘女士本人也是从这些文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她两次陈述都谈到这点。第一次她是这样讲述先祖盗头的故事的:
定:那你们家后代对您先祖怎么盗头的有没有传下什么故事来?
佘:那没有,就说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夜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就偷偷地埋在我们的后院里。你想袁大将军是这么一个重臣,罪名又是反叛,当时北京四九城都关闭了,当时在北京的广东人挺多的,跟着袁崇焕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别人都不敢。唯有我们先祖,深知袁大将军的为人和忠诚。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所以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1630年8月16号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我第二次访问佘女士时,再次问到佘女士如何听到这个故事的问题:
定:您这些袁大将军的故事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
佘:我父亲死得早,我是听我伯父和蔡廷锴呀,蒋光鼐呀,叶文伯、柳亚子呀,聊天儿。我们家的事我为什么听得那么多呢?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过去我们家是大家庭,我又是女孩子,一来客人根本不让女孩子在跟前儿,我们家的墙不是砖砌的,是隔扇。中间不是有空隙么,我就从空隙那儿听。我妈也老给我讲这些事,说你们家的事怎么怎么样啊。
定:有一个叫张伯桢的人您知道么?
佘:知道。听过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张次溪的,张次溪是张伯桢的儿子。龙潭湖那儿是张伯桢的家庙,因为他很佩服袁崇焕,所以他把袁崇焕也搁到他的家庙里了。张次溪写过《北京一条街——佘家馆》,1956年写的。我见过他,北京大学的教授,胖乎乎的,戴个眼镜。
定:他们家跟你们家有来往么?
佘:有来往,因为我们是同乡啊,我们是广东人,他们也是广东人,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还有叶恭绰、章士钊。
定:张次溪的后代和你们还有来往么?
佘:……不太清楚了,我也希望找到他们的后代啊。
这就是说,首先,佘女士只能将佘家世系上溯到第十四代,而这个第十四代,正是辛亥革命时期袁崇焕被重新彰显的时期。
这个故事至少到佘女士这一辈,不仅已经不再作为家训郑重其事地传授给子孙,甚至也无人谈起。既然如此,佘女士隔墙听伯父与蔡廷锴等人所述之事,肯定另有所本,其根据,很可能就来自张伯桢所撰:“佘义士墓志铭”。因为张伯桢与佘女士所说的蔡廷锴等人既是同乡又是来往甚多的同道。
佘女士提到的另两个事实也耐人寻味。
其一,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地点。既然故事从佘义士到刑场盗取袁崇焕头颅开始,刑场也就是盗头的地点,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明朝北京的刑场在西市,到清朝才改为菜市口。但佘女士却说,听老人说袁崇焕死在菜市口,因为她大伯每到袁大督师的忌日,都会到菜市口的斜街去祭奠。
其二,佘女士去过老家,即广东顺德。她说佘家在那里确是一个大户,她还参观了佘家祠堂的遗址,但无论从家谱还是口碑,都未能找到佘义士的线索。
这两点,权且当作佘义士故事有文人杜撰成分在内的旁证吧。
2.关于袁崇焕的籍贯
我第二次访问佘女士时,她明确表达了对袁崇焕纪念馆布展的不满,其中谈到袁崇焕的籍贯问题:
佘:(袁崇焕纪念馆)到去年好不容易给恢复了。定老师也知道,我们不愿意离开那儿呀,他们强迫我们离开(哽咽),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跟外界有任何联系,把我们跟外界的联系给割断了。您有时间去一趟,您看看他那个展览搞的是什么,展览的东部都是明代的武器,西部有七八幅照片吧,有五幅六幅都是说袁大将军是广西人,是袁大将军爷爷的衣冠冢,袁崇焕的衣冠冢……就是某个学术权威他说了,袁大将军是广西人,那你这开放是为了宣传你的学术观点呢?还是为了宣传袁大将军的伟大事迹?袁大将军亲自指挥的三个战役,哪怕一个战役给搁到里边呢,起码北京战役应该搁到里边展览吧,他是为保卫北京而死的,他如果不到北京来他还死不了呢。北京人更不应该给他忘记。
……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史家说法概括起来有三,即为广东东莞市、广西藤县和广西平南县,各有所据,莫衷一是,而一度以阎崇年的广西藤县说注30占上风。因与本文主题无直接关系,不赘。在我看来,袁崇焕的籍贯究系何处,与宣传袁大将军事迹二者间并不矛盾。佘女士何以会对袁崇焕是广西人一说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我曾经颇为不解。但是,只要了解佘家史事之由来乃至袁崇焕诸纪念物与广东的关系就可得知,袁崇焕的籍贯,其实是一个与佘家守墓之事有着不寻常关系的问题。
北京市崇文区(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那个旧日的“佘家馆”,佘女士说是广东义园亦即墓地,但在北京市的一些正式文件上,则是作为广东在京的几十个会馆之一对待的。这些会馆自1951年开始,便被逐步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有关部门。1956年,民主人士蔡廷锴、叶恭绰曾致函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称:“明代袁崇焕墓、祠堂及南海会馆戊戌议政处所等,均与文化史迹有关,袁武墓祠且经前岁李任公与弟等请市府修葺,颇壮观瞻,此次一并移交市府接管。此为两粤在京特殊纪念物,至今乡人和华侨来京均前往探访,此如何由市政府特别管理,免于一般房产等,视望商市府同人速定办法,以慰众望。”王昆仑接信后非常重视,当年的4月3日,市文化局经实地勘察后,便向市政府提出具体保护措施:
第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为众所周知之所,具有历史意义,拟由我局文物组接管,该处计有房产23间,住户多家,只北房三大间空闲,可由我局通知文化馆、站利用,其余房屋商由市房管局动员住户迁出后,一并交文化馆、站,以达到又保护、又利用的原则;
第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上嵌有康有为、梁启超石刻,有文物价值,可由文物组接管(后文与袁崇焕事无关,略)。
当年7月王昆仑对此正式批复:
第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物组接管,并保留北房三大间,作一横匾,加以保护(市领导注:不必迁设文化馆,不动员居民搬家);
第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嵌康有为、梁启超石刻,由文物组接管保护。注31
这段过程,佘女士有过简略的讲述,当然她是从自家待遇的角度讲的,佘家馆也由此而得以保留,直至建立袁崇焕的纪念馆。
北京的袁崇焕纪念馆于2002年年底开放,此时的袁崇焕已经被作为一个民族英雄,而不仅仅是广东乡人和华侨前往探访的“两粤在京纪念物”。地域的特点被如此淡化,今天的年轻人无所谓,老一辈却不以为然,我也是看到这些文件之后,才恍然明白佘女士对于这个“广西藤县籍”有所不满的原因。
3.其他
佘女士的二次述中,对于我提出的佘家多年来靠什么维持生活的问题也做了回答:
定:您爷爷后来是做什么?
佘:我爷爷不工作,自从我们葬了袁崇焕的脑袋以后呢,我们就辞官不工作了,就做老百姓了。我们家过去很有钱,我们是南方人哪,我们从南方一来,就把那边的地都买下来了,原来那块地方的名字叫佘家营,我们家地方大呀,就把我们家弄成一个广东义园,在北京的广东人死了,暂时不能运到南方去的,就埋在我们家,但是也没有碑,就是坟头。你要是来查,不知道哪个是袁崇焕的坟,哪个是别人的坟,因为都是坟头,只有我们一家知道,这是袁崇焕的坟,这是我们先祖的坟。为什么不叫广东义园?因为这是我们家自己的院子啊。光佘家花园一号就一顷多地呢,15亩啊,光这一个院就这么大。还有佘家花园2号、3号、4号。那边广渠门中学路北,铁路多高,那片大坡地多高,从夕照寺得爬个大高坡下来,南边到大马路,全是佘家的。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没人,就是荒野一片。
我们家地也多,(园子)前边租给粪厂子,他们给我们钱。城外的地是租给别人种,到年下给我们交租子,什么8个磅7个磅的,几口袋是一个磅。我们一共是3个园子,一个是龙潭湖那个,也是我们家的,请了一个姓刘的,刘老伯帮忙看着。因为我们佘家人少,辈辈单传,没人去看那两个地方。我们家房子也多,房后头还有枣树,长了枣呢,就把枣卖给枣贩子,你要几棵,4棵,5棵,打下枣,给我们钱。我们家还有买卖,听说还开着一个发廊似的什么。还做一种刮绒活。到我父亲那代也做刮绒活。不过我父亲他们自己不做,请人来给我们做。刮活是出口的,把蚕丝绑在一个木板上,然后牛骨头做的刀这么刮,刮出绒来。
而最令我感兴趣的,乃是她祖父过继给旗人的问题,以及对她祖父、父亲作为旗人的生活状况的描述,这在我对她做的第一次访谈中也提到了:
佘:我爷爷为什么叫佘恩兆呢?就是因为哥儿几个都死了,就剩我爷爷一个人了。过去老年间迷信,说我们家孩子不好活,您家孩子多,好活呢,就(把我们家孩子)给您。我爷爷的父母就把我爷爷过继给别人了,就过继给在旗的了。原来咱们北京在旗的都在哪些地方您知道么?东直门外头,往南一点,都是老在旗的地方。
我父亲家是个大家庭,我爸爸叫佘选增注32。我有5个姑姑,还有我大爷和我爸爸他们哥儿俩,一共是7个。
我们家特爱听戏,我父亲他们都是票友,青衣、花旦、老生,都有。我爸爸是唱黑头的,我大伯是唱青衣的,我大姐、二姐都唱青衣,我三娘儿是唱须生的,我舅舅是唱老旦的。马连良、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都在我们家唱过堂会,就在我们家那大厅里边,就是现在袁崇焕纪念馆的大厅。我们家还一客厅,现在已经拆了。那客厅要比那大厅还好,高台阶,客人来了就到客厅里边喝茶。
定:就是相当气派了。那个时候你们家那么多的朋友,包括好多名人和名演员,他们光是因为和你们家关系好,还是冲着佘家守坟的故事来的?
佘:那可能是知道的吧……我父亲跟我大爷,他们俩都特别高,这是他们的照片(看照片)。可是哥儿俩性格决然不一样。我大爷是凡人不理的劲儿,特别有架子。我父亲外号叫小白菜心儿,因为我父亲长得比较漂亮,性格跟我大爷也完全不一样,我父亲这人挺豪爽的,又抽烟,也喝点酒,还有个喜好是喝茶,早晨起来就喝茶。他爱交朋友,是什么人都交,什么捡煤核的、拉排子车的、倒水的、卖烧饼麻花的,都爱上我们家去。我大爷就说他么,就跟他和不来。
我们家比较复杂。我就知道有个姑奶奶行三,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我的三姑奶奶我还见过。我大姑奶奶婆家姓彭,我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给的是哥儿俩,姐儿俩给哥儿俩,也是做官的,那支已经没了,我那表哥要是活着的话也七十多小八十了。三姑奶奶婆家姓杨。比我爸爸大的我们叫姑姑,比我爸爸小的我们叫娘儿,北京人都这样叫,汉族人也这样叫。二娘儿,三娘儿,七娘儿。
我伯母不是别人,就是我奶奶的外甥女儿,他们是两姨成亲,我奶奶的姐姐的姑娘,给我奶奶做儿媳妇。我奶奶不是旗人,是汉人,姓王。我可不知道她是在哪儿。可是我奶奶的姐姐她们婆家是北京人,老在旗的,姓岐,就是一个山字,一个支字那岐。那个岐东贵,我管他叫爹,就是我爸的表弟,他是我爸的大姨的儿子,又是我大妈的娘家弟弟,又是我大爷的小舅子。我们家跟清朝是对立的,可是到最后成了一家人了。(看照片:中间那个是我姥姥,那是我母亲,那是我父亲)
这多少回答了有人提出的她家本是旗人却冒充汉人的疑问。但是从中也可以断定,他们对清朝、对满族的仇视至少在清朝未亡时早已消失,后来的那些感情和逸事,都是辛亥革命排满时被重新激发起来的。
佘女士的口述涉及的另一问题,是乾隆朝建袁崇焕祠、墓的由来。她所说乾隆帝寻找袁崇焕后人之事,是有史实为据的,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零,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复奏。
在访谈中我曾反复询问袁崇焕是否有后人之事,佘女士的答复都是否定的。但据《实录》,袁崇焕却是有一个后人的,他的嫡堂弟文炳曾过继给他一个儿子,其五世孙名袁炳,乾隆帝也确实给了他一个佐杂等官。注33按此仅为一说,另一说为袁有一遗腹子,后因军功入宁古塔正白旗,有张江裁(张次溪,江裁是他的名)撰袁氏世系为证。据此表载,袁的六世孙富明阿曾任江宁将军、吉林将军等职,其子寿山、永山均于清末在中日、中俄交战中以身殉国。注34该文并有孟森先生作序。注35王钟翰教授也曾注意及此,撰文考证过袁崇焕后人的入旗与“满化”问题,并将其作为300年来满汉之间从“兄弟阋于墙”到共同“外御其侮”的实证,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此处就毋庸赘述了。注36
佘女士在我做第一次访谈时曾为我详叙她自“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保护和恢复袁崇焕墓奔走呼号的经过。但事实上,袁崇焕墓的恢复之不顺,与很多人对佘义士盗头与守墓的故事一直持将信将疑态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这种质疑并非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早在20世纪50年代叶恭绰等人向毛泽东上书时,这一疑问就曾被有关专家学者提出来过,至今也仍然不断有人提出。我一度曾想搞清的,是讲述者的态度,她究竟是明知故犯的编造,还是自己也相信这一故事的真实性?至少到目前,我还希望是后者。
考订这一史实的真伪固然重要,也是史家的责任。但是这个故事,我毋宁将它看作是一个传奇,这对于我来说还有别一层意义,那就是看人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怀着怎样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公众的,或者是私人的)、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史实来编故事,这样的故事反过来又对这些编故事的人的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张伯桢为袁崇焕修庙立碑,为的是寄托报效中华的壮志,到他的儿子张次溪这里,已淡化成为文人寻访古迹的追思。佘女士的呼吁之所以会在近些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会成为近年来北京人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则是因其对叹息信仰缺失、理想缺失的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佘义士守墓的传奇,就是这样借助历史影响到活人的生活,又借助活人的解读变成了活的历史。因为至少,如果北京历史上真的曾有佘义士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存在过,对我们来说,也是精神上的一个慰藉。
4.张伯桢史事补记(2015年)
为佘幼芝女士和与此事有关的张先生做访谈,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正当我整理这部旧作准备出版的时候,竟又不期然在电视节目中见到已经久未谋面的佘女士,尽管此次是因为仍然为袁大将军祠等事奔忙,而与女儿发生矛盾,并诉诸媒体,我却为她的依然健康和依然执着而高兴注37。佘女士正在沿着十多年前的道路继续前进,我本来也不拟再对这个故事加以任何探究和修改,但无意中发现的有关张伯桢的记载,在这里却不可不提。这便是《档案》杂志1993年第2期披露的民国著名的“认祖门”一事,文曰:
洪宪帝制既成,有东莞张伯桢者,巧施媚袁之术。先伪印明版由汉袁安至明袁崇焕的《袁氏世系》一书,又编袁崇焕遇祸后,子孙某支由东莞迁项城始末,精抄成书。顺德罗某为之题册曰:“袁氏四世三公(当时推袁者皆美其为汉代四世三公之后)振兴关中,奋有河北,南移海隅,止于三水、东莞,清代北转,项城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名德之后必有达人”云云。书由梁士诒代呈项城,项城大喜,各部遂会衔奏请尊祀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原庙,项城又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漂水一城(伯欣)闻之,作《新华打油诗》注38以讥之,诗云:“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伯桢字),乱替人家认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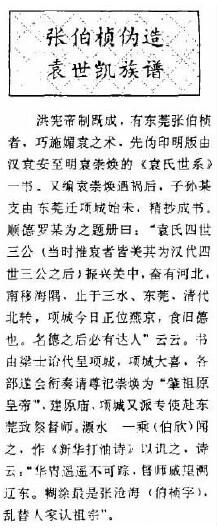
《档案》杂志刊载的张柏桢“认祖门”原文
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一事。袁世凯(1859—1916)是河南项城人,所以当时人称他“袁项城”。清帝逊位,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就是此文中所称的“洪宪帝制”。此举由于各方反对并引发护国运动,导致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被迫将帝制取消。袁本人也于1916年6月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张伯桢为袁“认祖”之事遂寝,然而,无论对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做何评价,张伯桢此举之荒谬和不光彩,也是难以否认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立人的文章提到“倚袁之力,张伯桢为袁崇焕刻文集,建祠庙。袁庙碑刻绝大多数为康有为撰书”。注39这一是说明张伯桢为袁崇焕刻碑立祠等行为,并不仅仅是我先前以为的崇拜英雄,或一般性的兴汉那么简单。二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和赞助,张伯桢也未必有如许的财力完成此举。
而且,我在上文中提出的疑问,看来也有了答案。我注意到张伯桢之子张次溪记述佘家史事时,语气与清人笔记一致,奇怪他为何采用清人说法而不取其父的修订。可知张次溪对其父的《东莞袁氏族谱》系伪造,心知肚明。
还要说明的是,有关张伯桢的“认祖门”一案,我是通过在网络上的搜索查到的,如果没有搜索时的这一发现,我可能至今仍停留在对他崇敬英雄之举的感慨上。这既让我有“学无止境”之叹,深感仅凭臆想便做出结论、发表感想,的确误人。同时也预感到由网络与数据库的兴起而引发的一场史学上的变革(即黄一农教授称为“e考据”的变革)即将到来。由于口述作业所涉社会层面的广泛性和不可预知性,将e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引入口述史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注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