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19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的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
当20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
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偲”以至“麦喀士”。
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2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1]: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紧接着,1899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
到了1902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190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1852年11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Commune”译成“公社”、“工团”,因此“Communist Party”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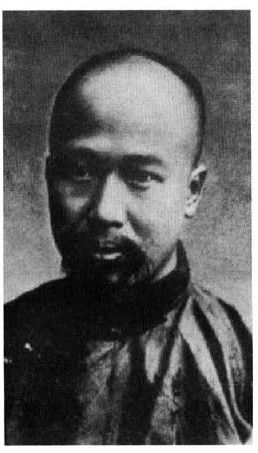 康有为
康有为 梁启超
梁启超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Communist Party”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1912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迄今,仍可以从1912年3月31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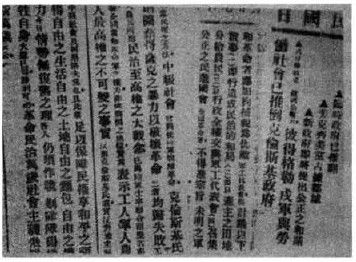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详细地予以报道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详细地予以报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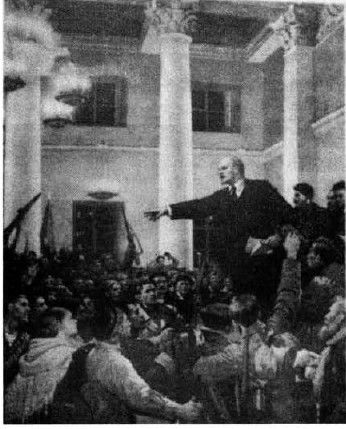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以深刻的影响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以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
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
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11月10日,上海由叶楚怆、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
“里林”何人?哦,“Lenin”,列宁!
《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11月11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十月革命的经过。
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
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1918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
这位邵力子,乃消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教师,那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以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
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好多位教授与他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
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
“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
“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
“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
 李大钊
李大钊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堂,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lshevism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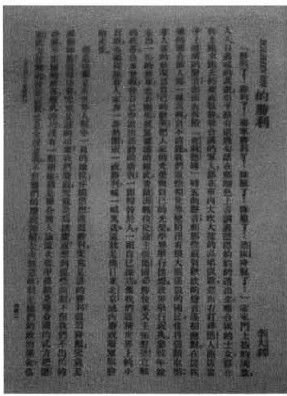 李大钊发表文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称颂俄国十月革命
李大钊发表文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称颂俄国十月革命 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愻(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亦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1]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1898年原版本。[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